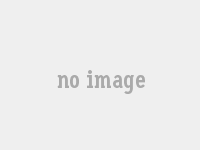1920 年,上海《解放画报》刊登了一幅讽刺画。配文曰:“辛丑革命,排满很烈,满洲妇女因为性命关系,大都改穿汉服,此种废物,久已无人过问。不料上海妇女。现在大制旗袍,什么用意,实在解释不出。有人说:‘她们看游戏场内唱大鼓的披在身上,既美观,到了冬天又可以御寒。故而爱穿。’又有人说:‘不是这个道理,爱穿旗袍的妇女都是满清遗老的眷属。’近日某某公司减价期内,来来往往的妇女,都穿着五光十色的旗袍,后说若确,我又不懂上海那来这些遗老眷属呢?”
这问题提得很有意思,旗袍形似旗装,虽然是有诸多改良、变化的,但以男性视角来看,与旗装大同小异,被认定是同一种服装也不为过。可让画报作者想不明白的是,大清朝都已经亡了,女人们为什么还爱穿着前朝遗物招摇过市呢?
上海不比北京,自然是没有那么多“遗老眷属”的,但“冬天又可以御寒”确实是一个实用的原因。民国之后,新派改良旗袍兴起以前,仍穿旗装的确多是些较为老派的女性,所穿旗袍也多沿袭清代的宽阔式样,因为连身保暖,故而也被称为“暖袍”。于是从功能实用的角度考虑,上海一到秋风转寒的时候,很多女性都穿起夹棉、衬绒或毛皮的旗袍,而面子用艳丽的绸缎,既很美观又可御寒。徐郁文在《衣服的进步》中说:“到了民国十年(1921),我们女界多风行旗袍,旗袍一行,我们女界到了冬天可便宜得多了。”
开风气之先——欢场的时尚先锋
旗袍在上海从实用转向时尚,第一拨转变却是由青楼女子完成。
老上海有条“四马路”,又名“福州路”,路的东段汇集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时报等一众新闻出版业,是条文化街;而西段则妓院、娱乐场林立,是老上海著名的红粉街。民国初年,上海大部分的新式服饰不是产生于设计师的头脑中或者裁缝铺的剪刀下,而是来自于青楼、舞场中女子的交际需要。她们的服饰,需要最华美的修饰和最新奇的样式。
“因为花间女子在穿着上绝不囿于成规旧矩,她们知道什么样的服装可以招揽更多的生意,什么样的服装可以让自己脱颖于众花之中,故大胆时髦,对服饰心理很有研究。”所以风月场所的女子们就成为了引领时尚的消费先驱。早在晚清时,徐珂的《清稗类钞》便记载:“同光之交,上海青楼中之衣饰,岁易新式,靓状倩服,悉随时尚。”因为身处租界的关系,青楼女子们还以出游为时尚(不会被视为“流莺”或以有伤风化论处),“不遍洋场不返家”,在社会公共空间充分地展示她们身上的“奇装异服”,因此“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
娼与优从晚清开始成为上海的社会明星,上海人亦步亦趋地学习她们的穿着打扮。据时人记载,清末的官僚多喜欢购买娼优为侧室。“妇女妆饰的改革多创始于娼妓。官宦家的侧室多出于勾栏,其妆饰当然与娼妓一律,富贵人家的妇女再相率效仿,于是新式的妆饰便可传染于上层人家的闺阁了》。”(权柏华《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妆饰谈》)
民国时期亦是,1922 年的《红杂志》上有一段记载:“不领之衣,露肌之裤,只要妓院中发明出来,一般姑娘小姐,立刻就染着传染病,比什么还快…”“时髦”一词的出现,就是对这种风尚的最佳诠释:“时髦”一词最初是上海人对乔装打扮、穿着时新的妓女,优人的称呼,如“时髦倌人”“时髦小妹”等,后来喜着时新衣装的人愈来愈多,“时髦”两字就不再为妓优所专有了,时髦的词意内涵也丰富起来”(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70—1910)》)
民国初年,上海的汉族妇女穿旗袍的并不多,但到了 20 年代初,旗袍首先在青楼女子中流行起来,时人记当时名妓唤作林黛玉的喜穿旗袍:“老林黛玉异时流,前度装从箱底搜,一时学样满青楼,出风头,一半儿时髦一半儿旧。”继而良家妇女看到那些新奇时髦的装束吸引了自己丈夫的眼球,便也开始模仿其打扮,所谓“女衣悉听娼妓翻新,大家亦随之”。更有从良为妾的妓女或舞女,将时新旗袍从欢场穿进了宅院,富贵人家的女眷再竞相效仿,于是旗袍日益流行,变得“近来上海女界旗袍盛行,闺秀勾栏,各竟其艳。”
女学生的“文明新装”
1924 年元旦,《申报》上一篇文章《妇女装饰别论》将当时上海妇女的着装分成了六派,分别是闺门、阀阅、写意、学生、欧化和别裁。其中“学生”这一派,同样是新潮服装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在 1898 年经元善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女学”之后,女子校服的问题就引起了关注。1906 年晚清新政进入第二个阶段,慈禧通谕全国兴办女学,《大公报》借此风潮不是在建议如何办学,而是发表《中国女学生服制议》,将女学生的装束问题当作女学兴盛与否的关键进行讨论:“夫国家之强,必以兴女学为要领,而女学之盛,则以改服制为嚆矢,若然则女学生服制之议,固今日谋国者之主要问题也。”女学生穿什么就决定着国家能否强盛?中国人以服制为立国之本的传统观念,在此时以近乎荒谬的论调表现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09 年,中国已有各式女子学堂 308 所,女学生14054 人,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教会女校及其女学生(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这些女学生们的服装讲求整洁、大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她们的装扮为社会各界关注和效仿,影响力一度达到顶峰,被称为代表新时代的“文明新装”。
初期女学生的学生装学自日本,短袄搭配黑色长裙,喜欢在发髻上戴蝴蝶花,常配以围巾,在国内受日本影响的新派人物中很受欢迎。旧派人物则对其不以为然,认为新发式徒有其表,脖子里挂一根白围巾的习俗又好像自缢的杨贵妃还魂,还作诗讽刺:“两扇一幅白绫拖,体态何人像最多?摇曳风前来缓援,太真返自马嵬坡。”(《申报》1912 年3 月 30 日登谷夫《咏沪上女界新装束四记》)
因为女学生要做操,在学校就要穿裤装,这在保守人士看来又很不顺眼,因为此前只有妓女才穿裤,良家女子都该穿裙的。可女学生们也不管这一套,不仅操课时穿裤装,有些人索性就把裤装当作便服,整日穿着上课,甚至从学校外出也不换穿裙子,引得教育厅发文训诫,说女学生“举止佻达,长袜猩红,裤不掩胫(小腿)”,实在没有个自重的样子,要求她们“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以正风气。
民国初年随着上海开放女学之风日盛,女学生也成为社会各界注视的焦点。十里洋场追求时髦是当时上海人的普遍心态,清纯女学生的形象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在当时,“女学生”是一个戴着荣耀光环并隐含着一些革命意味的名称,“时髦”一词远不足以形容女学生这一群新潮人物出现时所显现的光彩和魅力,因而女学生的着装一度成为社会时尚的引领者。
女学生装虽然承袭上衣下裙的传统模式,但是上衣逐渐缩短与腰齐,袖短露肘或呈喇叭形露出手腕,裙子逐渐上缩,裤子也缩短露出小腿,将身体曲线都展现出来。上衣的下摆不再有开衩。而处理为半圆弧形,既给下身的活动预留了空间,又省去了开衩包边的烦琐。女学生的衣衫都比较朴素,较少用簪钗、手镯、耳环、戒指等饰物,显出清新脱俗的样子。
20 世纪初,上海的女学生装中出现了新式的旗袍。新式旗袍首先以长马甲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女子将它穿在“倒大袖”(肩处窄、袖口宽的倒喇叭形袖子)的褂袄外面代替长裙,称之为“旗袍马甲”。
当时社会上正在讨论女子服装应当如何改良,1921 年《妇女杂志》曾有一篇文章写道:我国女子的衣服,向来是重直线的形体,不像西洋女子的衣服,是重曲体形的。所以我国的衣服,折叠时很整齐,一到穿在身上,大的前拖后荡,不能保持温度,小的束缚太紧,阻碍血液流行,都不合于卫生原理。现在要研究改良的法子,须从上述诸点上着想,因此就得三个要项,注重曲线形,不必求折叠时便利,不要太宽大,恐怕不能保持温度。不要太紧小,恐阻血液的流行和身体的发育。”旗袍马甲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女子服装的种种诉求,迅速风靡全国。
稍后,对服装不断求新求变的上海女性又将长马甲与里面的褂袄合二为一,省去上身重叠的部分,改成有袖的式样。衣身宽松,线条平直,仍是倒大袖,下摆至脚踝或小腿处,在领口、袖口、衣襟、下摆等部位镶滚一两道花边作为装饰。与清末的旗装相比,去除了烦琐的装饰,降低了衣领,缩短了袍身,改变了袖形,面料变得轻薄,费时费工的绣花也改成了印花。后来旗袍的样式变化还要满足女学生的要求,校园旗袍比社会上女性穿着的裙摆更要提高一寸,袖子更要剪裁合体,以便女学生们跑跳自如。
旗袍进入了校园,成为女学生们喜爱的装束,为这种来源于民族、重兴于世俗的女袍增添了青春感和高贵感。经过这些变化,改良旗袍变得精巧又便于日常穿着,已经为大规模的流行做好了准备。
顶着“文明”的标签。新派人物纷纷对女学生装趋之若鹜,上海各界女性视之为时尚纷纷仿效。随着穿着旗袍的女性越来越多,旗袍阵营中也区分出派别来,大致有公馆太太派、女学生职业女性派、舞女明星派三大群体。同穿旗袍,各群体之间却泾渭分明,半点也不能含糊。前两派终归受到身份限制,不能过于招摇。“教会女中的学生平的一身布旗袍校服,唯有周末回家才可稍做些打扮。她们不会穿紧绷着身体,线条毕露的旗袍,那是交际花和舞女明星的装束。”(程乃珊《上海百年旗袍》)
追时尚之潮——旗袍的时尚演进之路
当旗袍经过了青楼与女学堂里的改良和传播,大规模地回到社会公众的视野中时,已经形成了颇具声势的时尚潮流。当时的流行刊物《良友》画报总結道:“中国旧式女子所穿的短袄长裙,北伐前一年(1925)便起了革命,最初是以旗袍马甲的形式出现的,短袄依旧,长马甲替代了原有的围裙。……长马甲到十五年(1926)把短袄和马甲合并,就成为风行至今的旗袍了。”
从传统旗装中新生的旗袍流行起来,新时尚自然就激发出不同的社会声音。有人喜欢旗袍的线条,周瘦鹃(1895—1968)便认为:“妇女的装饰实在以旗袍为最好看。无论身材长短,穿了旗袍,便觉得大方而袅娜并且多了一些男子的英爽之气。”也有人讽刺旗袍源自清代的旗人旗装,清朝亡了却又流行“旗”袍实在不成体统,应当将其改名为“中华袍”(《袍而不旗》,《民国日报》1926年2月27日)。大军阀孙传芳甚至扬言要取缔旗袍。但是这些关于名称和民族归属的争论都没能阻挡旗袍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
就以孙传芳本人为例,他时任浙、闽、苏、皖、赣五省军政最高领导,公开发表反对女子穿着旗袍的言论,可是他有位受宠的姨太太周佩馨,学美术出身,偏偏对旗袍情有独钟,公然穿着旗袍去杭州灵隐寺烧香,根本不给孙传芳留面子。对此,孙传芳除了感叹“内人难驯,实无良策”之外也毫无办法,所谓的取缔,就更不可能执行了。
后记
我们今天谈起旗袍,脑海里总会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好像旗袍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可实际上在旗袍被普遍穿着的那些年中,经历的变化之多,绝不逊于一部时尚大片。
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滩的旗袍形成了一个产业,从中外衣料、丝袜配饰、各派裁缝、百货公司到广告、明星,无不围绕着旗袍款式的潮流而骚动着。近代上海与外来文化交流密切,此时的国内面料市场上,可供旗袍选用的面料种类除了丝、纱、绸、缎、棉等中国传统面料之外,还有从欧美等国进口的各种新式纺织品,如乔其纱、金丝绒、塔夫绸、尼龙绸等。这些进口面料质地柔软、富有弹性,并且价格相对低廉。
为都市女性制作旗袍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进口面料风靡中国市场的过程中,西式印花布逐步取代了厚重的织锦面料,印花工艺逐步代替了耗工耗时的刺绣工艺,节省了制衣时间和成本,使得旗袍这种女性时装有了成为“快消品”的可能。
当时穿旗袍的太太们,特别是经常在外面周旋的交际人物,几乎每周都要做旗袍新款,一位陆太太后来回忆道:“这个礼拜今天王家请客,再就是沈家请客,如果总是老一套(旗袍),别人就会说怎么这么寒酸,衣服都没有。所以当时一定是要这个样子的,这就是当年的风俗,大家要交际,没办法,那时候总是拿旗袍翻花头(做新样子),常常要换得,一直穿要穿厌掉的。人家请吃饭什么的,我总是最晚到,我的先生一直说我,你总让人家等。我喜欢磨蹭呀?穿衣服么,床上放了很多,穿这件不对,穿那件也不对……”(蒋为民《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1929 年,成都的一首流行诗写道:“汉族衣裙一起抛,阿侬出众无他巧,花样翻新好社交。”所指也是同样一种需求。